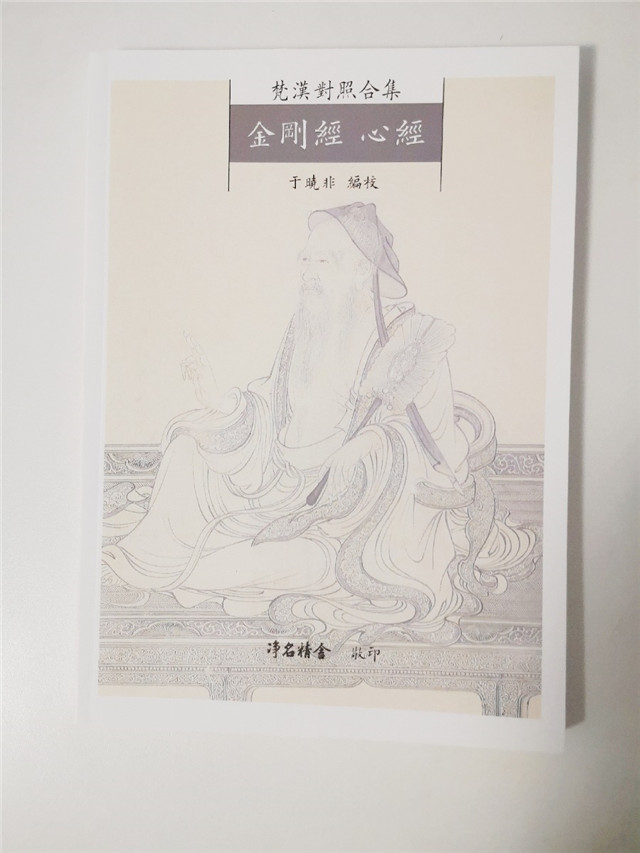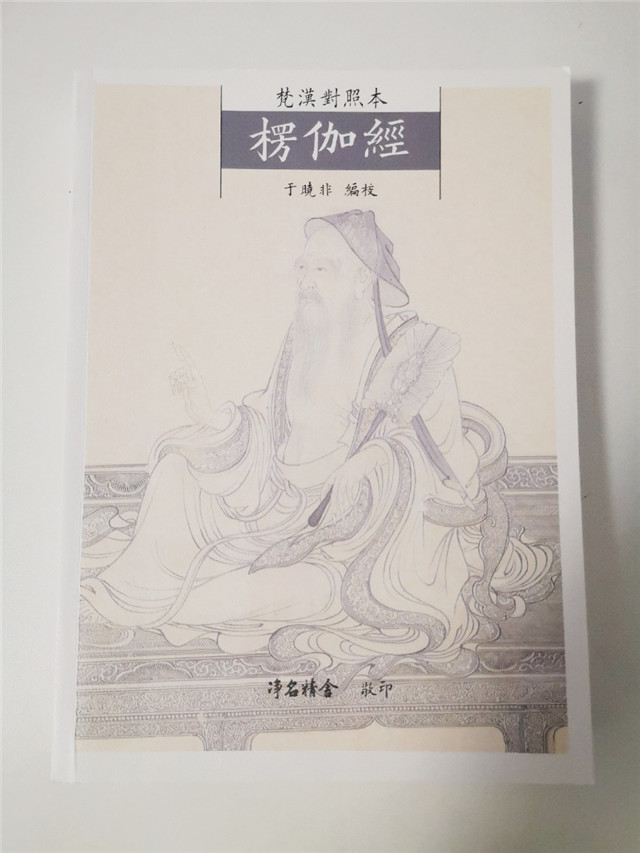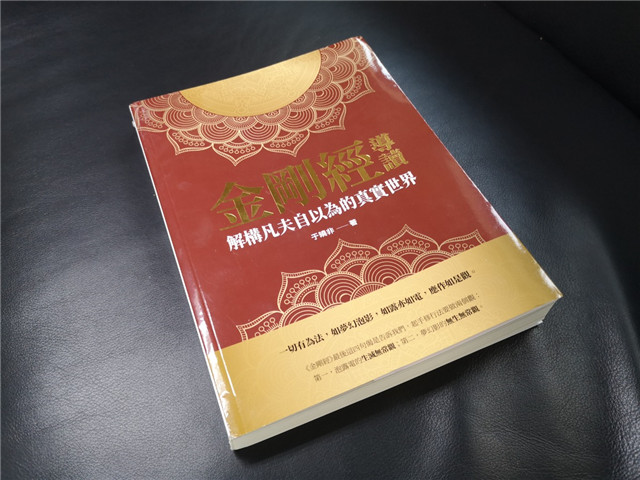文 / 秦占國 張寶峰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外物、自身、內心,通常被視作三個不同的維度,需要不同的調處之道。中華文化傾向認為,儒學適於入世應物,道學適於舒放人身,佛學適於探問內心。這三者的相互交融也構成了中華文明的一大特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
近日,著名佛教文化研究專家于曉非在北京接受了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的獨家專訪。這位對物理學、東西方哲學都有著深入研究的學者說,漢傳佛教的近代復興經歷了坎坷波折的道路,目前自己屬於第四代接力者,而且是一位堅守原教旨主義的佛學傳播者。于曉非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迎來了一個開面包容的新時代,這為漢傳佛教的近代復興提供了寶貴的土壤。
于曉非能夠把艱深的佛學思想深入淺出地闡釋出來(受訪者供圖)
21歲那年,于曉非在普陀山普濟禪寺了空法師處受三皈依,後進一步受教于韓鏡清先生。談及自己在佛學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于曉非認為,一方面得益于當前這個開明包容的時代,另一方面也有賴於漢傳佛教復興史上前三代大家所奠定的基礎。“我是這個復興鏈條上的第四代,而且是大乘佛教的原教旨主義者。”于曉非對自己的認知與定位一直非常明確。
于曉非的佛學課一直廣受歡迎(受訪者供圖)
開設線上講壇
談起第四代人物對佛學復興的獨特貢獻,于曉非認為,其一,自己試圖恢復的是大乘佛教的本來面目,不是小乘教法,更不是相似教法。為此于曉非悉心學習梵文、巴厘文,堅持忠於佛陀的原教旨主義精神。其二,自己對於大乘佛教的理論梳理格外清晰曉暢。“人們總說佛學博大精深,但博大不等於龐雜,精深不等於晦澀。”為此,于曉非務求將佛學理論闡釋到平白如話的程度。其三,儘量選用現代人熟悉的語彙。
點開喜馬拉雅上的《金剛經》導讀課,于曉非的聲音娓娓傳出:“鳩摩羅什大師把《金剛經》的名字翻譯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部佛經的名字,大多是佛親口所說……從這個名字來看,《金剛經》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法門——般若波羅蜜。”向來被認為艱深晦澀的佛理,變得清晰曉暢起來。APP統計資料顯示,僅第一講,播放量就超過280萬次,整個《金剛經》導讀的播放次數更超過3225萬。很顯然,于曉非的佛學課深受聽眾喜愛。
“一堂課講得再對路,如果聽眾根本聽不懂,又能弘傳多少佛法呢?”在講座或撰文的時候,于曉非都堅持“隨順眾生”的理念,讓人看得清聽得懂,“但隨順眾生並不是迎合眾生,更不能將弘傳佛法變成分享心靈雞湯,隨順眾生的目的最終應該為了接引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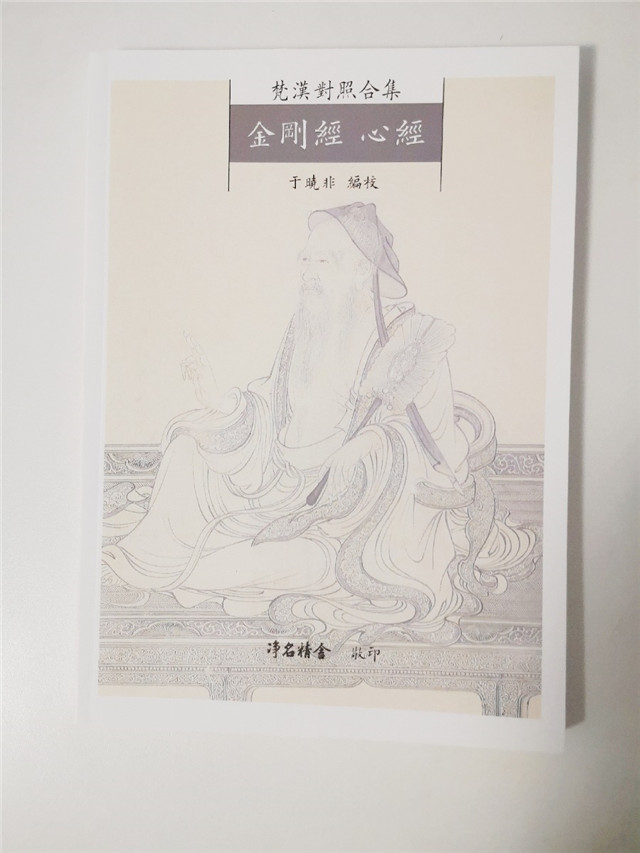 于曉非編校的《金剛經•心經(梵漢對照合集)》(記者秦占國攝)
于曉非編校的《金剛經•心經(梵漢對照合集)》(記者秦占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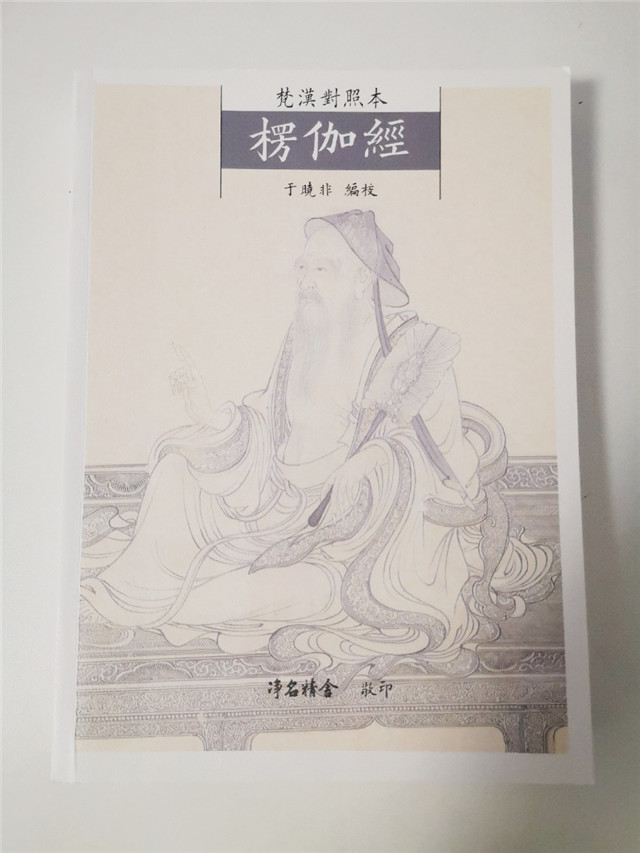 于曉非編校的《楞伽經(梵漢對照本)》(記者秦占國攝)
于曉非編校的《楞伽經(梵漢對照本)》(記者秦占國攝)
如今,除了已經在聽眾中間取得熱烈反響的“《金剛經》導讀”、“《楞伽經》導讀”外,于曉非還計畫講授另兩部經典——《中論》與《阿含經》。“講完這四本書,我就基本完成了作為第四代復興者的使命,我也可以真正退休了。”于曉非笑著說。
完成平滑解構
于曉非所著《解構凡夫的“真實”世界——《金剛經》導讀》(記者秦占國攝)
在《〈金剛經〉導讀——解構凡夫自以為的真實世界》一書中,《權便中觀》與《究竟中觀》兩個篇章最有特色,也包含了于曉非最多的心血。在《權便中觀》中,于曉非構建了平滑解構的四重二諦,而在《究竟中觀》中,于曉非完成了對“二邊見”的徹底泯滅,將佛陀所言的中觀境界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佛教文化中,唯有佛陀是清醒的覺者,普羅大眾都是常在夢中的凡夫。在對世界的理解上,佛陀與凡夫自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正因如此,佛陀如果徑直講授自己對於世界的理解,凡夫註定無法立即接受,因此凡夫只有先放棄自己對世界的既定觀念,才能逐漸接受佛陀的理念。“但如何解構凡夫對世界的理解,卻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于曉非說,自己在《權便中觀》中構建的四重二諦,就是一種平滑解構,讓凡夫在悄然間意識到自己的錯謬之處。
在完成解構之後,于曉非開始闡釋自己對於佛陀中觀理論的理解。“1500年來,很多人都認為,不走左路,不走右路,單走中路,就是佛陀所說的中觀。事實上,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有左有右,而後取中,一方面與儒家的中庸之道難以區分,另一方面依然留有二邊見的遺痕。”于曉非說,事實上,只有徹底泯滅二邊,也就是說既無左路,也無右路,才是佛陀所說的中觀,才是最為徹底的中觀,也才是空性意義上的中觀。
現代社會須備“好刹車”
在人類繁衍生息的過程中,宗教始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麼,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現代文明如潮奔湧的背景下,宗教的意義和價值又在哪裡?談及這個問題,于曉非首先打了一個比方,“眾所周知,一輛車子若想安全地上路行駛,必須有兩套系統:發動機與刹車。而且發動機越好,刹車也需要越好,否則就難以實現制動功能。試想,人類社會何嘗不是如此?”
“如果把人類社會比喻成一輛車子,那麼,科學、技術,正是扮演了發動機角色。它們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類的各種欲求。但是,如果只有發動機,沒有刹車,後果是不是不堪設想?”于曉非說,事實上,宗教正是發揮刹車作用的一種文化,它收束著人類不合理的欲望,為社會發展注入理性和冷靜的因數。
于曉非認為,當今時代,科學發展,技術進步,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就好比“發動系統越來越先進”,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匹配“更加先進的制動系統”,換言之,人們就需要保持更大的理性與克制,保持更篤定和純粹的信仰,讓社會朝著更加文明的方向邁進。
理科生眼中的“三條線”
在大學時代,于曉非的專業是天體物理學,堪稱純粹至極的科學科目。然而,他最終卻成為一位知名的佛學專家。談到對科學與宗教的看法,于曉非的見解同樣非常獨到,“科學、宗教、文藝,分屬三條不同類型的線條。”
“科學的基本特點就是發展,從伽利略到牛頓,從愛因斯坦到霍金,科學一定是以後來者對前輩學者的否定、更新或完善而實現發展的。如果在科學的範疇內,說哪一種理論無法發展,那麼,它一定是面目可憎的。”于曉非說,如果為科學畫線,它一定是一條向上滑行的曲線。
“與之相反,宗教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可發展性。”于曉非認為,無論釋迦摩尼,還是耶穌,還是穆罕默德,都在各自宗教創立之初,就給出一套完備自洽的理論體系,它不需要也不允許後人去修改、完善,而只有解讀、信奉。因此,宗教就像一條不斷向下的曲線,離初始教主年代越久遠,人們對教法教義的理解可能偏差越大。
于曉非進一步說,文化藝術的特點是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位高峰式的人物,譬如貝多芬、蕭邦,又如徐悲鴻、齊白石,但絕對不能說後人的藝術一定是走臺階式地不斷超越前人,也不能說後來者中就再無高峰式的人物。因此,文藝的曲線更像不斷起伏的波浪。
譚嗣同與“無我為眾生”
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傳入中國經歷了三條路徑:其一,從印度傳入斯里蘭卡,又傳到東南亞地區,最後到了中國雲南,是為南傳佛教,亦稱小乘佛教;其二,從印度翻越雪山,來到中國新疆,又傳入中原地區,一直抵達朝鮮半島、日本島等地,是為北傳佛教、漢傳佛教,屬大乘佛教;其三,從印度直接翻過喜馬拉雅山,進入中國西藏,是為藏傳佛教,亦屬大乘佛教。
僅就漢傳佛教而言,其在隋唐達到鼎盛,有宋一代尚存餘脈,進入明清則是全面衰落。以致于到了清末民初,佛教一度淪為“死人的宗教”,也就是只有老百姓家裡操辦白事,才會想起找個和尚念念經,超度超度亡魂。不過凡事否極泰來,佛教也在衰頹至極之時,迎來了復興的迴響。1866年,一個29歲的年輕人約集朋友,廣募資金,在南京創辦了金陵刻經處。選覓善本,大量刻印,同時辦學,講授佛理。這個年輕人就是近代著名佛學家楊仁山,後世尊其為“近代漢傳佛教復興之父”。
回憶起楊仁山先生,于曉非首先提到了楊的一位弟子。“1898年,清光緒帝頒佈《定國是詔》,決意變法。當年,一位正在楊仁山先生席前聽講的學生突然奉詔入京,受命參與變法。後來,戊戌變法失敗,這位33歲的年輕學子慷慨赴死,成了中國近代為變法而流血的第一人。”于曉非說,楊仁山先生的這位高足就是譚嗣同。“譚嗣同身上展現的就是大乘的菩提心,完全無我為眾生,這才是大乘佛教徒的風範。”
除了這位名垂青史的入世門生,楊仁山還有兩位佛學造詣極深的出世弟子:太虛和歐陽竟無。後來,太虛傳印順,印順傳證嚴;歐陽傳經與呂澂,韓鏡清聞法于歐陽。“因此,在漢傳佛教復興的譜系上,楊仁山先生是第一代,太虛、歐陽是第二代,印順、呂澂、韓鏡清是第三代,證嚴和我都屬於第四代。”于曉非表示。
【于曉非簡介】
于曉非,1961年11月出生於北京,畢業于南京大學天文學系天體物理學專業。大學畢業後,一直任教於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科技哲學與現代科學技術教研室。現為淨名精舍首席學術導師。
1982年,于曉非在浙江省普陀山普濟寺了空法師處受三皈依,法名根培。曾親近過正果法師、巨贊法師和觀空法師,受教于賈題韜居士、任傑居士和韓鏡清先生。1996年9月至1999年1月,于曉非在北京大學東語系師從段晴教授和王邦維教授學習梵文,師從斯里蘭卡比丘學習巴厘文。就印度思想文化諸多重大問題,曾請教于徐梵澄先生和金克木先生。
在學佛歷程中,于曉非深入經藏,潛心修持,對於佛教的歷史淵源、法脈沿革等都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深入研究。近年來,于曉非組織了大量弘法利生活動,令許多人士因此生起正信,獲得法喜。于曉非也被譽為“當今內地最受歡迎的弘法居士”。
于曉非已出版代表作包括:《〈金剛經〉導讀——解構凡夫自以為的真實世界》《楞伽經(梵漢對照本)》《金剛經•心經(梵漢對照合集)》等;于曉非在喜馬拉雅音訊平臺播講“《金剛經》導讀 ”和“《楞伽經》導讀”課程,受到數千萬聽眾的喜愛;于曉非的線下講座主要包括:《二諦與三性》《佛學漫談》《佛陀——覺者》等。

于曉非編撰的佛學系列著作在讀者中間很受歡迎(記者秦占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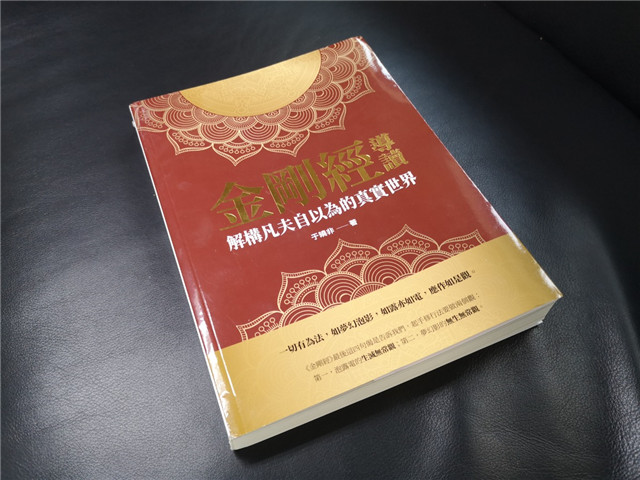 于曉非撰寫的《金剛經導讀——解構凡夫自以為的真實世界》(記者秦占國攝)
于曉非撰寫的《金剛經導讀——解構凡夫自以為的真實世界》(記者秦占國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