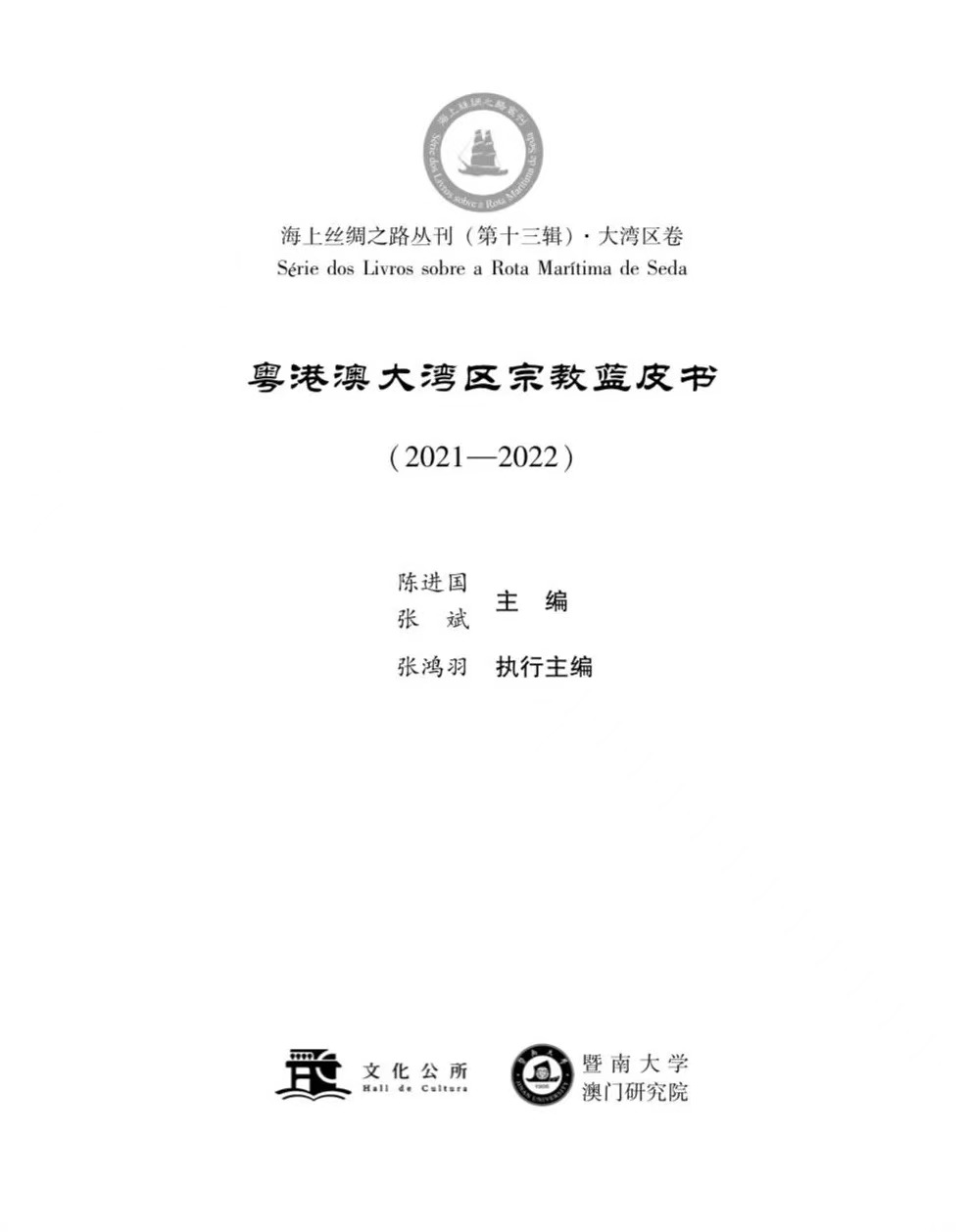2021年,渥承廣州的暨南大學將《粵港澳大灣區宗教藍皮書》正式納入“海上絲綢之路叢刊•大灣區卷”的出版計畫,“2019-2020”卷雖是新鶯初啼,卻有幸獲得了學術界和新媒介諸多的支援和鼓勵,當然也不乏善意的批評。不少學友希望我們繼續組稿,讓各界可以從一個“灣區共同體”的視野,去整體地觀照各種宗教和信仰形態在灣區內的存在樣態,並對比性地“共感”各自所面臨的發展處境。承蒙三地學術界、宗教界諸賢的鼎力支持,在疫控中我們只能勉為其難,編成了“2021-2022”卷。
其實,所謂藍皮書者,無非是一群學人之獨立的觀察與多元的觀點之彙聚罷了。誠如梅洛-龐蒂所言,現象學世界是“在我的各種經驗的交匯處以及我的經驗與別人的經驗的交匯處的、通過一些經驗與另一些經驗相互嚙合而隱約顯露出來的意義,主體性與主體間性因此是不可分割的。它們通過在我的現在經驗中再現過去經驗、在我的經驗中再現他人的經驗而形成它們的統一”。宗教藍皮書基於現實性關懷的觀察,即通過親歷性和肉身性的相互嚙合的體驗,只是反映了一種將地域宗教的歷時性歷史包裹進共時性結構的努力,反之亦然。而文本自身的“人為性”則是“通往普遍的第二個通道:不再是突出在一種嚴格客觀的方法之上的普遍,而是作為我們通過人種學的經驗,即不斷讓自己接受別人和別人接受自己的考驗而取得的一種側面的普遍”。是故任何針對宗教藍皮書的另一種現實性的“想像”“期許”或“懷疑”,也是多餘的。《莊子·則陽》有一則“少知”與“大公調”的對話。丘裡之言遵循“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的歸納邏輯,“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大人合併而為公”,成為一方習俗公論,但丘裡之言真能推出反映普遍秩序的“同是”“公是”否?大公調的回答是“不然”。宗教藍皮書最多展示的是地域宗教“側面的普遍”罷了。我們在洞察作者們彼此嚙合的“偏見”“異見”時,更需要培養一種“情感性共感”,在“情境性”中體認作為多樣性的他者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宗教”(Religions)。
毋庸諱言,儘管粵港澳新隸屬於同一個地理意義上的“灣區”,“地域相近,文脈相親”,但歷經數百年來的獨立發展,其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畢竟差異頗大。像內地和澳門主要隸屬於大陸法系,而香港是以英美法系為主,也帶有多元化法律體制的特點,各自在法律淵源、法律適用、判例地位、法律分類、法律編纂和訴訟程式等方面都有差異,由此三地在涉及宗教治理的法律條文和法例規定更是各彰其彩,從而參與形塑了各自的宗教文化生態和宗教可持續發展格局。所謂“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灣區宗教和信仰形態的多元性、豐富性、共融性,更是灣區自身持續充滿“複合性文明”活力的神聖源泉和歷史記憶,需要各方本著“
同情之默應,心性之體會”的態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既要尊重現實,更要展望未來。是故,堅守“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宗教平等”“宗教和諧”等基本原則,當且僅當成為一種當下暨未來的“灣區共識”。而這種灣區共識是跟文化意義上的灣區人盈溢著精神性的生活世界、生命世界息息相關的,涉及我們基於良知和理性的道德經驗、普遍福祉。
2019年中國政府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導“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這種指向未來志向的話語構建雖然感覺歲月美好,卻真正需要灣區人基於地域歷史之勢能的自主捲入。而灣區人要堅定文化自信,豐富精神內涵,自然離不開宗教界對在地社會的靈性加持和心靈守護。然而,“宗教與社會”如何調適共融一直是一個恒久的話題。在一個以民主、自由為核心價值的“灣區共同體”構建中,“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與“發揮東西方多元文化長期交融共存的特色”,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本無所謂文明間的優越與落後之分。而構成一個開放和文明社會的先在條件,是既要警惕因特定宗教之“排他性”的自身特質而衍生的“零和擴張”的衝動,更要反思故步自封的文化民族主義的“抱團取暖”。事實上,無論是香港、澳門還是以廣東為橋頭堡的內地,在應對自身的殖民化、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種種困惑時,根本不存在兩個地域空間(港澳/內地)在族群、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對峙的現實性,也無法承受自我想像的對峙所帶來的實驗性或災難性的後果。誠如列維納斯所言:“他者並不是向觀看而是向領會顯現的”。領會需要彼此的“親歷性”,更需要源自主體自由的“移情”與“共感”。
毋庸諱言,灣區的創設,本身就是一個嘗試“反轉”內部性的、地緣性的對抗性框架(東方與西方,內地與港澳)的產物。它既是對港澳以“內地”為鏡像的主體性塑造的“超克”,也是對內地以“港澳”為“西方(殖民)”的客體性想像的“超克”。但我們應當清醒看到,灣區作為一個構想與規劃,本身尚不具備一種實體性的意義,而是像竹內好筆下的“亞洲”一樣,“處於主體的形成過程中”。灣區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作為一個“地方”的世界,同樣存在於不同區域(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東莞)的相互關係中,而不可能以某種普遍性的形態存在於不同的區域之上。因此,倘若脫離了自身區域的主體性,只能意味著依附於其他區域或區域外的主體性,同樣意味著你無法進入不同區域間的相互關係中,亦即你實際上脫離了“灣區”,陷入假裝自主性、獨立性的區域化陷阱。作為過程和行動的灣區的前景不需要樂觀主義的假設,而是需要立足于灣區人的普遍福祉的“同是”(價值觀)的歷史重建。
是故,曾經持續彌漫在灣區內部的種種風波和事件,儘管與區域內整體的生活世界和集體生命經驗(也包括宗教經驗)相關,也必將反復構成流動性的、創傷性的區域歷史敘事,但反觀其人其事,既有來自以“內地”為鏡像的區域主體性喪失的戒懼,也源於自身過度依附於“西方”現代性中的主體性迷思。在“想像的內地”與“想像的西方”之間的反復糾結,無疑在自我“製造”一種正在或者已經喪失的“優等生”的文化面容或政治戀情。地方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幻景儘管賦予了集體的經歷和期許予深刻的歷史意義,卻也面臨著如何以“虛己”的勇氣來智慧地處置象徵化的記憶碎片。是故,倘若灣區內部的群體依舊抱持著階序性的身份認知和悲情陳述來相互啃噬,所謂基於“情感性共感”的灣區共同體的“有機團結”的構建,也就必然喪失了一種朝向現實和未來的可能性。
內田樹曾經以地理學、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邊境性”或“邊緣性”來分析日本人的思維和行為取向,認為日本人有“東張西望的普遍精神狀態”,總在尋找更強的“保證人”。丸山真男則強調日本人對於外來意識形態的國民性反應類似於“固定低音”,它永遠成不了主旋律,只能在低音部反復徘徊。或許,我們可以沿用與“中心性”對應的“邊陲性”來勉強領會灣區“邊陲人”的精神氣質。百年以來對外來殖民化的思想意識形態或制度文明資本的挪用、借鑒,是被近代性所塑造的“邊陲人”的先天優勢,使之既是現實主義者,也是機會主義者,善於抓住時機,接納新思想,具有改革、開放、包容、認真的集體品格,並形塑了“東方之珠”的自主性、優先權、決定權。曾經在“香港人”“澳門人”意識中的“內地人”“中國人”的標識,並非意味著“中國認同”的消解,而同樣是一種清晰的“距離意識”或“邊陲意識”的條件反射。
反之,當下開始形塑南方地域准中心的“廣東人”“深圳人”,在近觀“香港人”“澳門人”,內心卻天然沉澱著來自天朝、天下的“中心-邊陲”的縱深景觀,常常是在“中心”的邊緣(境內)來看圈外的“邊陲”(境外),並通過想像近距離的他者形象,來塑造“中國人”的中心意識。這種以中心自居的內地主體意識,似乎伴隨改革開放的成就而被強化,甚至產生了一種逆向的“優等生”的俯視心態。灣區內族群記憶的等級化和階序化的迅速倒轉趨勢,也意味著各區域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貌合神離的,並非真正的平等夥伴或鬆散的聯合體,尚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中心)來進行有效的統合。或許這是介於“中心-邊陲”模糊地帶的灣區的宿命也是使命?
套用並置換竹內好的話語風格,我們必須誠實指出,“境內”與“境外”的語詞分辨,意味著所謂實體性的灣區文化與一體性的灣區政治是不存在的,甚至有來自“中心——邊陲”的對抗性的思想基因。灣區並非存在於各個區域之上,而僅僅是存在於各個區域的“力學關係”中,而“世界”或“全球”或“國際”則存在于灣區之外。只有灣區內不同區域的文化、宗教的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創立所謂灣區現實的和未來的總體文化形態。換句話說,只有灣區內的文化、宗教彼此“打破”灣區內的文化、宗教,才有創造出新的灣區文化、宗教,所謂灣區共同體意識的鑄造才是現實可能的。因此,“作為方法的灣區”,現實和未來都更需要一種互為背景、互為他者的平等互視的機制。除了範導我們精神性的生命意義的宗教和普遍的至善,灣區內共通的“粵語”以及正在普及的“國語”普通話,同樣為構建基於他者倫理優先性的互視提供了可能性。
誠如思想家列維納斯所言,“我對他人的責任,這悖謬性的、矛盾性的、為了他人的自由而負的責任”,“並非出自對原則之普遍性的虔敬,亦非出自一種道德的明見性。這責任是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此關係中,同者會被他者所關涉,但他者卻不會因此被同者吸收。在此關係中,我們可以辨認出一種靈啟——在此詞嚴格意義上,即賦予人以精神”。因此,灣區的現實與未來並不需要“肩並肩”或者共契的集體性、統一性,而是迫切需要由“我-你”關係構成的親歷性、主體間性、共融性,“一種沒有仲介的面對面”,在彼此的嚙合經驗中相互理解、共感他者的將來性和神聖性。
在上述意義上,大灣區宗教藍皮書分類為“廣東篇”“香港篇”“澳門篇”,事實上是想努力呈現灣區三個區域在宗教信仰及宗教治理上的“力學關係”及其可能有效互動的實際樣態。事實上,作為編纂者,我們的話語立場只有一個,即對“一個灣區,各自表述”的尊重。然而,我們從灣區宗教的多元化表述中也會領會到,理解並推進灣區宗教間的雙向交流與情境性共融,對灣區共同體的文化統合是何等的舉足輕重。那些流行的、化約化的“中西”標籤以及“中心-邊陲”的宇宙觀和“境內-境外”的地理觀,並無助于人文灣區的話語構建。灣區是什麼,是否能成為灣區人的一種自我意識和直覺默會的理念,才是根本的問題。否則所謂灣區註定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虛相”和“概念”。
具體說來,本集的“廣東篇”皆是內地作者,他們的出發點,正是我所說過的,根據“政規教隨”的原則,來強調區域內的宗教治理如何走向善治、良治與“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之路。這樣的寫作思路,同樣是給灣區其他區域提供了一種關乎交往、交流邊界的他者性、陌生性、異質性的氛圍。“香港篇”涵括內地與香港的作者,介紹香港涉宗教治理的普通法條文及法團條例等,以及接受上述法律保護的香港宗教在教育投入、社會運用、慈善公益等方面的現實表現形態。這些文章其實反復提醒著灣區的“內地人”,如何在信守“一國兩制”、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則下理性地認知宗教在香港社會中的精神性地位。哪怕是同情地默會香港傳統宗教對於法條深受殖民化影響的“不公”心態,或者尚未能理解香港宗教在教育界和慈善界的傳統領導地位,亦必然在尊重現有的法律規範下去思考未來香港宗教在灣區中不變與可變的邊界。“澳門篇”同樣關注本地主體宗教與學校教育和公益事業的有機關聯,同時注意到新興的巴哈伊社團在中國區域的傳播及其構建服務型和學習型社區的面向。有心的讀者從灣區的三個篇章中,不妨以“情感性共感”的態度,去領略不同的寫作思路和思想立場,並從中省思人文灣區的未來性及灣區精神的可能向度。
毫無疑問,在灣區的宗教中“共感”大寫的“人”和“生命”的意義,才是學人、宗教人、灣區人應有的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