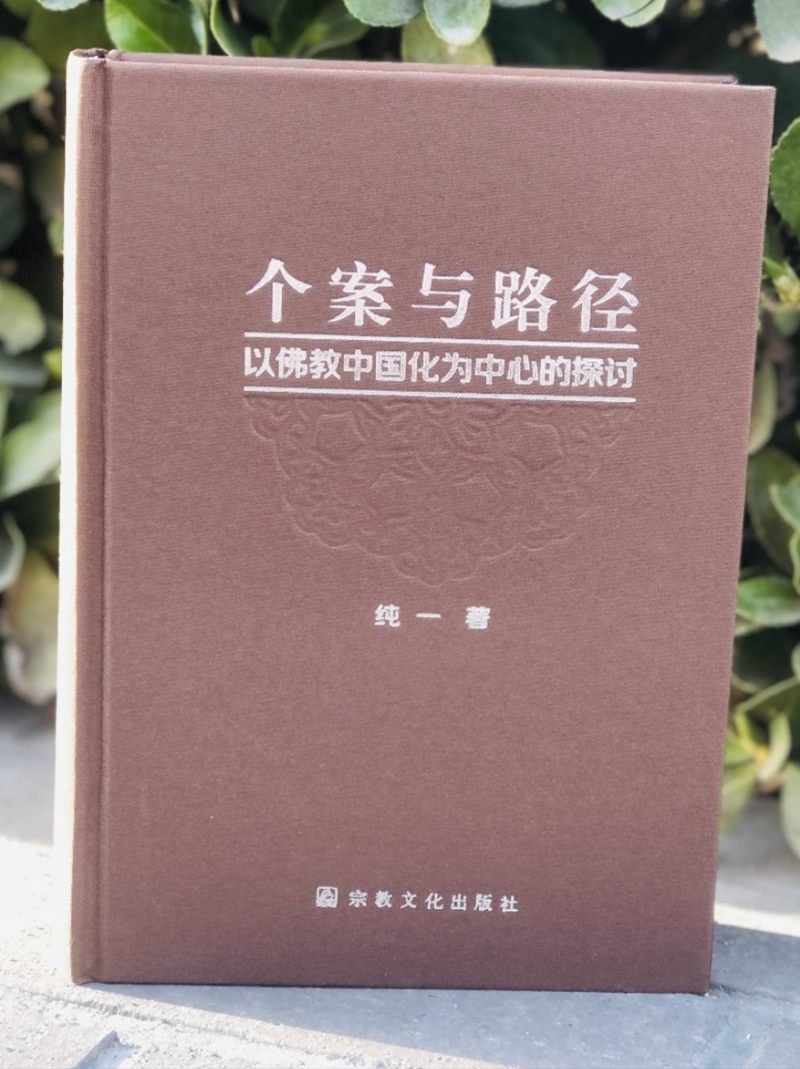陸夢龍 博士
純一法師所撰的《個案與路徑——以佛教中國化為中心的探討》一書,以11個專題研究為中心,從歷史和當下兩個維度集中展示了佛教中國化的諸多“經典場景”。研究某種宗教或者某個教派的興起緣由及其歷史使命,無論中外,其基本方法大致不出兩種:一是個體主義方法論(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強調個體行動及其結果才是所有行為分析的終點,而任何宏觀概念都只是導向這一結果的中間過程(Process),這一方法的首要提出者為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之后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又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二是整體主義方法論(Holistic Methodology),強調宗教的功能研究,致力于在形上的信仰與形下的利益驅動之間,構建出或曲或直的映射關系,這一方法又以涂爾干(émile Durkheim)的功能主義為典型。佛教中國化的歷史考察和實踐探索,同樣離不開上述兩種方法的自覺應用,該書以“個案”與“路徑”為標題,從方法論上更多地傾向于前者,而從作者對“人間佛教”的傾意和對經典文本分析的注重,則意味著對佛教傳承和發展的高度自覺,是佛光慈心的自然流露。從這一意義上而言,該書方法論的自覺意識與作者的深切用意,實現了方法與目標的高度統一:“個案”即為禪理的彰顯,“路徑”即為學佛的大道。
具體而言,該書以“祖師西來意”、馬祖道一、黃檗希運禪師以及文益禪師等個案揭示中華禪理的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和流化天下的歷史過程,從不同側面描述了基于個體參禪體驗和行動信仰的禪學面貌;不僅如此,作者還以“歷史記錄者”的個體視角,還原了虛云大師、太虛大師以及趙樸初等現代“人間佛教”踐行者、倡導者的濟世歷程,再次強化了個體覺解與濟世情懷相融相合的大乘精神。同時,該書還包含了若干佛教文本的考證分析,并將上述文本個案穿插于上述兩類專題研究中,既彰顯了作者學、行相融和理、跡一貫的禪學意趣,又生動地再現了今日“人間佛教”不斷創造的生命力。
一、禪學“個案”與禪理的現代意蘊
禪學個案的研究思路,無論是從禪學精神自身還是從宗教社會學的思路而言,都與個人主義方法論高度契合,為了理解這點,有必要將馬克思·韋伯和哈耶克對這一方法論的闡釋略加說明。
馬克思·韋伯在《經濟與社會》第一卷第一章“社會學基本術語”中進行了詳盡闡釋,他的前提是:行為(Behavior)可以是無意識的(例如打噴嚏),但行動(Action)是可以被理解和追述的(例如為剛才打噴嚏而道歉)。自然科學化的社會學家,往往以某種“后見之明”替代對個體行動真實原因的探討,從而喪失了對個體行動的基于主體認知的把握。韋伯并非不注重對集體行動的探討,而是旨在強調集體行動的多模型事實,并且初步總結了個體行動的四類背后動機: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情感和傳統。 韋伯這一方法論最終導致個人主義傾向的價值論,但這一點絕非這一方法論的初衷,而毋寧說,這一結果是這一方法論的自然副產品。需要指出的是,個體主任方法論所導致的個人主義,也絕非是霍布斯等人的原子式個人主義,因為他所關注的“個體”,實際上是有傳統、情感和理性等自覺意識為基礎的。
接受這一方法論并且集中闡釋這一方法論內在所隐含的個人主義價值研究優先原則的,則是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他在論文《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 中,集中闡述了這一方法的基本內涵。他批評當時所謂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往往將社會現象的研究牽引至當時自然學科業已存在的目的和結果導向中,而忽視了個體行為動機的千差萬別,讓社會科學(例如經濟學)陷入僅僅關注統計學數據關聯而忽略內在動機探討的怪圈。哈耶克認為,對于這類極端科學化傾向的學者而言,很多社會現象的“不可理喻”,其原因就在于離開了對個體行為的關注和透視,既然如此,合適的做法是重新回歸到對個體行為的理性考察當中,微觀的考察才是宏觀趨勢研判的基礎。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完全是理性主義者,相反,作為奧地利經驗主義傳統浸潤下的經濟學家,他認為個體的無意圖行動(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而導致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才是應當極力關注的焦點所在。
盡管上述兩位域外學者關注的問題域并不在宗教,但真正的道理是不分古今中外的,禪宗的“公案”和“話頭”傳統,可謂與個人主義方法論不謀而合;純一法師以“個案”研究隱指佛教中國化的“路徑”,也與這一傳統若合符契,可謂東西遙相呼應,古今冥然一體。
純一法師在“祖師西來意:對佛教中國化和中國禪宗創立的考察”這一專題研究中,便對“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進行一番“語言上的冒險”。成佛或者開悟,豈是預先能設定的“行動”?不能!未覺解前,事事皆是無明之行,覺解后反觀以往諸行,便豁然自覺。人人都是自證成佛的實踐者,“行為”在覺解下變成了可以被理解的“行動”,而“行動”又逐漸成為某種“傳統”,這便是禪宗“公案”的來歷。純一法師運用語義學的相關原則,對“達摩西來意”這一公案的內在旨趣,加以明白揭示。正如韋伯和哈耶克所言,今人如果太執著于“預定的”科學目標,完全不顧及個體行動的多樣態意識,那便極容易郢書燕說。唯有對個體行動的充分知曉和尊重,才有“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同一話題的30余則公案。禪宗的立教宗旨和傳播大江南北的根本動因,就在于不拘一格,因人設教,這些話頭可謂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這一“奧卡姆剃刀”法則的禪學表達。
禪宗流行,離不開歷代禪師的自覺張揚,甚至可以從哈耶克的意義上說,禪宗流化天下,完美地體現了禪宗是個體自覺行動而形成的“路徑”和“自發秩序”。在“黃檗法脈與天下三黃檗”個案研究中,作者巧妙融合了兩位禪師的個體史,講述了黃檗宗這一禪學法脈流衍的“道路”:出家于福清黃檗山的希運禪師,以黃檗為多重意向的象征,將他禪化天下所居的江西靈鷲山改為黃檗山,并隨著明清之際福清黃檗寺的隱元法師應邀來到日本,在京都傳播黃檗禪,將禪寺所在改名黃檗山,從而形成福建、江西、日本京都“天下三黃檗”的禪學盛景。希運禪師在出家時,何曾預料天下竟有三黃檗?!此種盛景的形成,就在于一代代禪師竟力向前,猶如人類知識和經驗的增加,得益于“千秋道振在斯時”(隱元語)的當下進取精神,此種精神絕非理性或者非理性這種分類法所能涵蓋,正是歷代無數“個體”禪師勇往精進,自覺開辟更多的“黃檗山”“黃檗寺”,才有今日的禪林盛況。從個人因緣而立“話頭”到自覺循行“菩薩道”,禪宗之相多隨時轉,禪宗流化也各有不同,但這種始終著眼于個體行動的起悟之方,始終關注個體生命覺解的大乘精神,才是禪理的真意趣。
從更廣闊的的意義上言,“佛教中國化”也屬于佛教研究的“個案”,這一“個案”的書寫,離不開“中國”與“佛法”的交互交融,而如何在當下展開這種互動,純一法師也將寓意隱藏于另一類型的“個案”研究中,即對太虛、虛云大師和趙樸初先生學行事功的記述。
二、“人間佛教”與大乘菩薩行
純一法師在該書《自序》這樣概括中國佛教的特質和精神:“中國佛教的特質就是大乘佛教,呈現給世人的就是菩薩道精神。”所謂大乘和菩薩道精神,以俗語概括,即為度人精神,而大乘佛教兼重自度和度人。由自性、自度而度人,猶如內圣而外王,似為某種通見,而由度人而自度,外王而內圣,更是大乘真義。禪宗流行以來,特別是南傳盛行之后,不立文字當下即性即佛的禪定修路,其簡易之妙,自不待言,但難免同時也產生一定的流弊,即所謂的狂禪習氣。如何避免這些末流弊端,大乘度人之教可謂是實其虛、防其弊的良方。
佛教有大小乘二派,佛教傳播也有中外之別。小乘佛教盛于中南半島,由中南半島而流播于東南亞諸島和斯里蘭卡,最終延至澳大利亞。從中南半島至澳大利亞直至歐美社會,佛教以某種東方神秘體驗文化的形象傳播于全球各地,各種佛教社團與同樣源自東方的瑜伽、冥想等修行俱樂部,猶如星羅棋布。佛理流行和參禪之風,相映成趣,由定而靜的習禪修禪,乃是普通西方人視角中的佛教印象。
從腦科學角度著眼,參禪、觀想、正念與冥想在意識層面都有某種相通點,即顯性意識進入某種有別于無所事事和自我游思(也可稱為“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的狀態,即所謂的“默認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 DMN),醫學界往往將這種入定稱為“關注當下的默認模式”(represent-centered default mode)。一個人平時大約有47%的時間處于無所事事的狀態(DMN),這種狀態極容易激發大腦的低落情緒,Matthew A. Killingsworth和Daniel T. Gilbert兩位心理學家曾通過一款名為HAP的網絡應用程序,讓參與者上傳自己當下即刻的狀態和快樂/不快樂感受,他們從25萬名軟件使用者中,選擇了來自83個國家的5000名參與者的狀態信息作為樣本,分析得出“大腦無所事事是不幸福的”(A Wandering Mind Is an Unhappy Mind)這一結論。 2011年,由多位高校精神病理學、心理學家合作,對禪定、正念、冥想深度參與者的大腦進行核磁共振掃描,從大腦功能和神經科學角度初步證明了參禪入定有利于精神壓力的減緩甚至有助于相關精神疾病的控制。 西方醫學界的相關成果,從科學角度佐證了包括禪定、正念、觀想在內的各種靜定之道始終具有普遍適用價值,禪宗也是極具當下意義的自覺自修的自我關懷之道。
戒、定、慧三者中,戒為最難,更何況是無師審察的心戒?入定修行與無所事事實為毫厘之別,而參禪入定,偷惰怠慢在所不免,其流弊也會不覺漸長。從腦科學角度看,無所依系、無所執念的禪定從長期上會顯著降低大腦相關區域對具體任務神經處理模式(task-specific neural processing)的反饋頻率 ,用俗語表示,即容易滑向沉浸于自我游思和對外界了無興趣的狀態。參禪之苦,入定之難,即在于此。歷代禪師對禪定流弊和悟道之難,深知三味,只有理解了他們的“現實”和“合理”主義眼光,才可明了作為禪宗高僧的純一法師,諄諄告誡以大乘和菩薩道精神的良苦用心,也同樣才能理解趙樸初等現代佛學大師追求“人間佛教”的深切用意。
基于這樣的背景,再看純一法師以“歷史記錄者”的視角,詳實記載了虛云大師、太虛大師以及趙樸初等現代“人間佛教”踐行者的言行事功,這種事功也是習禪學佛的妙音,由外王而更能證成內圣,絕非一句虛語。純一法師在回憶虛云大師的禪學風貌時,有兩語讓人敬仰不已:一是“始終倡導坐做并重或農禪并重”,虛云大師以自己的行禪習禪體悟,對于禪學流弊洞若觀火;二是常言“禪是無字之教,教是有言之禪,反對禪宗僧人以不立文字為借口不學經論”,可謂教禪并行、學悟兼舉。同樣,太虛大師將自己“人生佛教”失敗之因歸結于“禮論有余而實行不足,啟導雖巧而統帥無能”,也是對思、行如何統一進行了深刻的總結,而趙樸初先生則以“學佛就是要學菩薩行”開示世人,與太虛的精神宗旨相為表里,純一法師又再發妙音于后,中國禪學,可謂有人矣。
三、佛經文本與佛光普照
純一法師對學行相合之道,可謂躬行不已,對佛教經論、俗講變文、文史以及六藝之學,皆有精深獨到的研究成果。由學行相融這一視角著眼,便不能不對佛教文本研究與佛法發揚的關系問題加以探討,以明了作者遙寄千載的尊佛興教之心。
佛教或者說中國禪宗作為一種宗教團體,同樣也存在如何與時俱遷、與中華一道綿延賡續的“適應”問題。無論是“人間佛教”的正道理念還是“話頭”機鋒的委曲周詳,無不與時代息息相關。
以現代社會生物學進化為視角研究宗教的適應度問題,當以戴維·斯隆·威爾遜(David Sloan Wilson)和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最為引人矚目,前者所撰的《達爾文的城堡:進化、宗教與社會的本質》(Darwin’s Cathedral: 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主旨在于從功能主義的視角,運用達爾文所提出的“群體選擇”理論探討宗教和教派興衰和此消彼長的動因;后者所撰的《上帝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God)一書,則從基督教上帝觀念的演化史來推敲信仰之道的現實合理性,亦即對任何宗教的教外人士而言,所謂宗教信仰的“不可思議”往往與我們不了解其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密切相關,換言之,羅伯特·賴特是將宗教信仰基于個體在環境壓力下的選擇上進行叩問和追尋。如果從宗教社會學的學術淵源上判斷,戴維·斯隆·威爾遜更加接近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而羅伯特·賴特則更傾向于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上述當代社會生物學家的前沿性探索,正如宗教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采用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研究基督教的興起問題那樣,社會生物學家則在宗教組織、信仰文化等領域不斷拓展生物進化論諸種法則的“應用場景”,這也意味著,適用于生物學進化的基本規律和學說,從根本上也可適用于宗教組織和信仰文化的研究。
對于經典文本與佛教流衍的關系問題,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是,真正的社會生物進化論與19世紀中葉以來大行其道的社會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直生論”迥然不同,其中最根本的立場差異,在于前者強調社會進化的無目的性,即進化方向的選擇,是環境壓力和基因變異相互選擇的結果,而并不存在預定的方向。同樣,宗教組織和信仰文化的演變,也并不存在一個預定的“最優解”,佛祖何嘗寫完所有經典?如何保持宗教文化的內在活力,正如同如何生物多樣性那樣重要,這其中的關鍵因素在于處于邊緣地位的原始種群是否能夠得到足夠的地理空間和選擇機會。
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會有多次的文化復興現象,即“回到”古代尋找新的文化進化方向。這種文化的“返祖開新”并非是特例,而是因為邊緣的“原始種群”保留了最多、最具差異性的基因屬性,足夠讓某一種群面對環境選擇的壓力時,有較大的進化選擇的緩沖余地。
今人常言,欲滅國族者,先滅其文化和歷史,從社會生物學和生物多樣性角度來看,這一名言仍然具有真理的品格。佛教要實現賡續長存,那就必須保持對經論文本的敬意和“對話”,這些經典文本,猶如邊緣地帶的原始種群,它保留了一個宗教組織和信仰文化不斷適應時代變遷的“基因庫”。純一法師在論及“達摩西來意”,特意用較多地筆墨考證“祖”的內涵,這種自覺與社會生物學的基本規律,不期而相符。
如何保留佛教經典文本的“生存空間”呢?答案就在于時刻要與經典保持“對話”,即通過對佛教經典本文的整理、詮釋和分析,使之長存常新。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看,這種與經典時刻保持“對話”的研習之路,存在三個方面的必要性:
一、經典文本往往保留了環境選擇壓力的“文化印痕”,盡管環境已經迥然不同,但“印痕”仍在,仍是宗教組織面對類似或者同質話選擇壓力的文化記憶和信仰傳統。
二、經典文本承載了歷代書寫者的文化自覺意識,人類與動物不同,就在于從結繩記事開始,我們就創造了超越生物基因層面的信息傳承和保存方式,因而人類文化的基因庫,會在經典的注疏和經論中不斷得以保留放大,因而宗教組織之間的“生存競爭”,也會存在馬太效應:時間越久者,文化自覺越強者,生命力越旺盛。
三、經典文本的選擇和再解釋,其實就是一種創造力。宗教組織和信仰文化的進化,實質上是信仰者的自覺行為與環境變遷多重因素作用的“刺激”反應。
行文至此,今人當能明了,純一法師的“個案”與“路徑”研究,也從各個維度道出了“人間佛教”的未來之路。